在上世纪初的语言标准运动中,北方方言“战胜”了南方方言,成为全国通用语言。近年来,随着人们对中心化与去中心化、现代与传统、单一与多元的反思,对在地文化、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,逐渐反映在方言在文化作品的呈现上。

要了解一个地方,最好的方式,就是用当地的方言讲述当地的故事。方言播客就是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,但听得见、品得深的文化传承。
目前,有不少比较成熟的方言播客节目,例如沪语播客《上海往事》《嗲上海》《漫点讲》《谈吵烦》《横竖横》,粤语播客《尴卵尬》《香港嘢史》《讲东讲西》《收皮有限公司》,东北话播客《正经人电台》《赤电台》,四川方言播客《不摆了》,等等。方言播客虽然小众,但不乏忠实粉丝。

在方言播客中
声音从来都不仅仅是声音
五条人乐队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火起来的时候,有粉丝说,“不唱海丰话的五条人就不是原来的五条人了”。可见,方言也是身份认同感的一种。在方言播客中,声音从来都不仅仅是声音。它既是媒介,又是信息,不仅被方言所传递的信息编码,而且透露了说话者的身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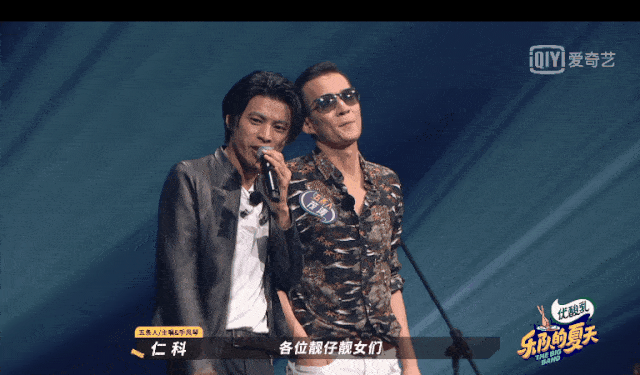 △海丰话是五条人的精髓
△海丰话是五条人的精髓有的艺术创作者不愿被贴上地域化的标签。他们只是在表达某种特定场景、某个特定人物时,使用了最合适的语言。反之,为了更好地呈现一种情境,在播客中,以方言讲述地方故事,是最为生动的。
梁文道的“看理想”团队正在推广“方言计划”,他们在自己的平台上引入来自不同地方的方言播客。梁文道说:“既然中国人在学习英语上能花很多时间,花一点时间了解方言,不行吗?我们不能忽略神州大地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方言。它们有独特的传统,有各自的面貌。身为一个中国人,假如能够多听懂几种方言,会对我们这个国家有更丰富、更全面的认识。”
“方言计划”中有一档粤语播客,名为《香港嘢史》,主播是作家马家辉。别看马家辉平时在《锵锵三人行》《圆桌派》里普通话说得不太利索,但用粤语讲起香港故事来,可谓生龙活虎、滔滔不绝。
为什么用粤语做播客?马家辉说:“理由很简单,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‘土著’,我的粤语说得比普通话流畅。最重要的是,因为我们这个播客讲香港的历史故事,用粤语的字眼才能说得特别贴切、准确,才有‘港味’。”
“比如我讲海盗张保仔的故事,说到张保仔和他的义父、义母有点暧昧关系,用普通话说是‘他们有暧昧’;用粤语来说则是‘他们有路’。意思虽然一样,但是懂粤语的人能领略那里面的感情色彩。”
 △香港故事当然要用粤语来讲/unsplash
△香港故事当然要用粤语来讲/unsplash和马家辉一样,作家何平也开了方言播客。何平人称宝爷,他当过老师、办过报、开过书店,还做过文学顾问,唯一不变的是,他一直生活在上海。他花了两年时间,做了名为《上海往事》的沪语播客。
何平说:“我在上海下了一辈子的功夫。什么叫一辈子功夫?就是一直住在上海,一辈子没搬场、没离开,在上海好好过日子,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吸收上海人的智慧。上海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城市,是一座值得从根上说起,枝蔓纵横、含义丰富的伟大城市。它的来龙去脉,现在被鸡零狗碎的弄堂八卦掩埋了,所以需要一点点学问来打捞。讲上海往事肯定要用上海话讲。”
 △和方言一样,上海的建筑也藏着上海往事/unsplash
△和方言一样,上海的建筑也藏着上海往事/unsplash有听众听了何平的播客,留言问他有什么快速学习上海话的方法,或者怎样才学得好。何平说:“我无力推荐什么好方法,因为我也想学,我想学一口老派的上海话,但是不得其门而入。上海话在方言市场的地位现在是日薄西山,当年则仅次于粤语。如果有人要学广东话,我可以推荐他去听学粤语金曲,粤语有非常直观的学习对象。遗憾的是,上海话几乎没什么可以推荐的。”
《新气集》主播李梓新,现居伦敦,他做的是潮汕方言播客。他说,这可能是第一个潮汕方言的播客。7年前,李梓新就希望推广潮汕话。为此,他发起了一个名为“听潮”的TED活动,现场嘉宾全部用潮汕话进行演讲。最高峰的时期,有上千人报名参加。
李梓新说:“现在是播客时代,我觉得用播客来开启‘听潮’是个很好的方式。”考虑到播客全部用潮汕话传播性可能不够,李梓新采用潮汕话和普通话相结合的方式,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潮汕文化。
 △传播潮汕文化,潮汕人还自己拍了电影
△传播潮汕文化,潮汕人还自己拍了电影
方言已然式微
传承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
北方方言与普通话更为相近,也更容易被书面记录;南方方言却常常难以在文字中找到对应的表达,因此也更难于用文字传承。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,多少听得懂东北话;但一个没有接触过南方方言的北方人如果点开一档南方方言播客,无论是粤语、沪语、潮汕话、温州话,估计统统不知所云。
“盖盖头”是一个沪语播客主播,目前定居海外。他说,决定用沪语做播客时,他有点犹豫,害怕粉丝认为他这是排外。
盖盖头说:“因为我在海外,所以想用上海话去采访在国外生活的上海人,聊聊他们的生活。有意思的是,我发现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上海家庭的孩子,还保持着说上海话的习惯。我见过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上海人,他只会说英语和上海话,因为家里人交流都是说上海话。没人教他普通话,所以他既不会听也不会说;反倒是上海话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了。反观国内,现在很多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孩已经不会说上海话,可能一两代之后,上海话就消失得差不多了。”
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


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





 热门资讯
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
